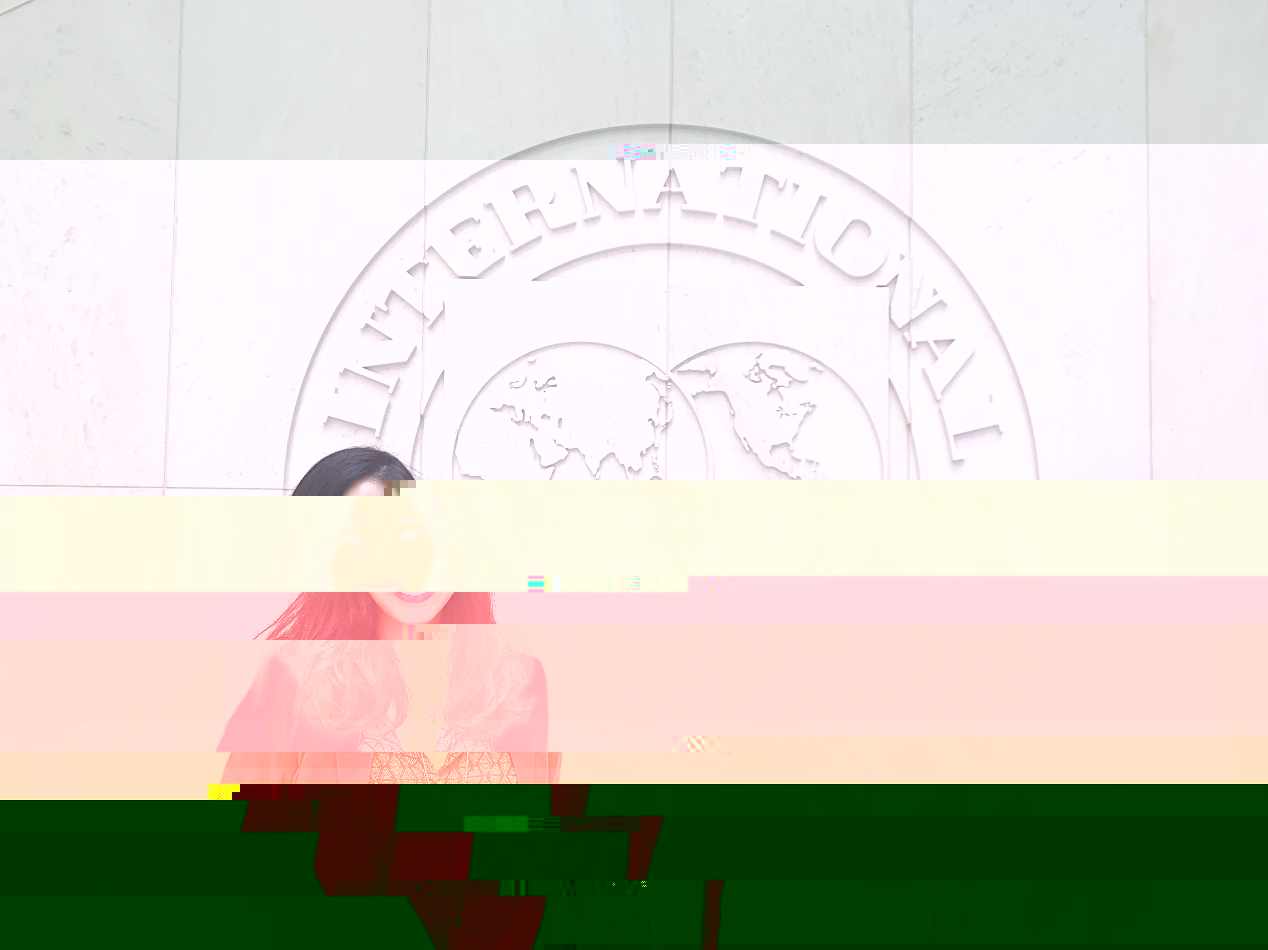
楊元辰,Betvictor中文版外文系學士,Betvictor中文版2014級金融碩士、2016級金融學博士,目前在國際貨币基金組織擔任經濟學家。
畢業後到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工作一直是我的夢想,在清華五道口讀書的6年幫助我夢想成真。
“有想法很好,關鍵是去做”
2014年我從清華本科畢業,保送到清華五道口讀金融碩士。到國際組織工作是我很早以來的想法,可在很長的時間裡都僅停留在想法而已,真正的轉折點是有幸在學院聆聽了朱民老師的演講後。作為在國際性機構中任職級别最高的中國人之一,朱民老師為我們講述了他作為金融外交家的職業生涯。提問環節中,我表達了自己希望能夠去國際組織就職的強烈意願,朱老師聽後鼓勵道:“有想法很好,關鍵是去做。”簡短的回答點醒了我,沒有付諸實踐的想法不過是空談而已。當天回來,我就詳細翻閱了IMF的人才需求,開始為此一步步地努力。
攻讀博士就成了我的第一個目标。順利讀博的第三年,在富布賴特獎學金的支持下,我選擇來到哈佛商學院讀書。哈佛給我打開了一扇嶄新的大門,給了我機會與最仰慕的教授合作,讓我收獲了科研水平的提高,也讓我學會舒适地與異國文化為伴。國内積累的學術基礎、豐富的科研經曆,加之對環境的迅速适應能力,讓我先後收獲了泛美開發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IMF的實習機會。
與實習更多的強調研究能力不同,IMF全職員工的選拔更多的是考察候選人是否具有成為一名經濟學家的潛力——既要能夠對成員國的宏觀經濟狀況進行分析,又要能夠為政策制定者提供可靠的政策建議。這就要求候選人不僅需要像所有博士那樣在各自領域的學術前沿有所突破,完成原創性的研究,同時需要具有理論結合實踐的能力,思考研究背後的政策意義。在最重要的面試環節,我被問到的問題涉及發達國家負利率、石油出口國的彙率選擇等諸多時事熱點,這些問題都沒有标準答案,面試官希望聽到的是候選人自己對經濟的見解和對世界的認識。
“做學問,就要耐得住寂寞”
求職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風順的。當科研的壓力襲來,當周圍的朋友紛紛找到了不錯的工作,每個讀博的人都會有陷入迷茫的時候,我也不例外。但幸運的是,我遇到了一位好導師——田軒教授。田老師從海外留學歸來,對我們的要求始終是做國際一流的學術。他辦公室的大門始終敞開,每學期都會和學生一對一談話,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的兩次談話。
第一次是在我開始寫第一篇論文的時候。當時我有幾個自認為不錯的想法,興奮地找到田老師。他聽後娓娓道來:驗證每個想法可以用什麼數據、需要注意什麼技術細節、執行過程中可能會出現哪些問題、文獻中的哪篇文章可以借鑒……無論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論文,還是最新一期的期刊,浩如煙海的金融學文獻似乎都印在了田老師的腦子裡,讓我大開眼界,受到深深觸動:自己作為博士生,連與想研究題目有關的文獻都沒有搞清楚。就這樣,我開始每周研讀經典論文,每天關注最新的學術動态。末了,田老師說:“你的想法不錯,是A級期刊的水平,但是想要達到在頂級A+期刊發表,還要培養好的學術‘taste’(品位)。”回來後,我把這短短的一句話品味了好久:學者的追求自然是突破學術前沿,但更高的追求應該是對社會有價值,對國計民生有貢獻。
第二次是在我對前途感到迷茫的時候。那是在博士三年級,一方面自己的論文進展不盡如人意,另一方面身邊的同學紛紛在籌劃三年甚至提前畢業。在朋輩壓力下,我向田老師表達了自己希望盡快畢業的想法,田老師聽後給我講了他自己求學的故事:從北大畢業後,他首先在美國讀完經濟學碩士才開始攻讀金融學博士。“我們在蓋的是一幢參天大樓,”田老師說道,“參天大樓需要紮實的地基,不在于一朝一夕。”回想起田老師的第一節課,不是金融學ABC,而是一堂“勸退”課——他用自己的經曆,給我們講述了順利拿到博士學位,乃至投身學術研究所要經曆的種種考驗。但實際上,我知道田老師幽默背後的良苦用心,他真正想說的其實是要做好學問,首先要耐得住寂寞。
如今工作後,我和田老師依然有着學術合作。一日為師,終身為師。我想這就是理想中的導師吧——為你的成就而驕傲,更重要的是在低潮的時候支持你,在迷茫的時候點醒你。
本土情懷與國際視野
研究中國經濟,沒有比清華五道口更适合的地方。五道口四十年的辦學曆史熠熠生輝,無數卓越的師兄師姐們從這裡畢業後,成長為業界精英、學術領袖和被委以重任的監管人才。
清華五道口吸引我的,不隻是這些響亮的名字,更重要的是其背後,深耕祖國金融實踐的光榮傳統。清華五道口的曆史見證了中國金融的發展史——她的畢業生們參與創辦了我國第一家法人股份制銀行、第一家上市銀行、第一家證券公司、第一隻基金……學院的發展始終與祖國發展的脈搏相結合。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正是我一直以來的追求。
除了本土情懷,清華五道口給予我們的還有國際視野。作為博士生,讓我受益匪淺的是學院與國際接軌的學術資源。每周各類學術講座,邀請來自全世界的優秀學者與我們分享科研成果;圖書館豐富的數據庫,讓我們放開手腳去探索自己感興趣的課題;更不用說那一流的硬件設施,以至于坐在哈佛商學院的階梯教室,我都倍感熟悉。
當我走出學院,與來自世界頂級高校的經濟學、金融學畢業生競争,我絲毫沒有感到技不如人,反倒是本土情懷與國際視野的結合,讓我在數千名申請IMF經濟學家崗位的經濟、金融學博士中脫穎而出,成為多年來唯一一位從中國大陸院校博士畢業的入選人。
跳出舒适圈,擁抱大舞台
把外語特長與金融背景相結合,将經濟研究融入政策建議,在國際舞台上講好中國故事——我從事的正是自己一直以來最向往的工作。如今的我,每天從事着三方面的工作:
代表IMF與多國政府談判磋商,協助宏觀經濟金融政策的頂層設計。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發展中國家,首要任務都是如何盡快控制疫情、恢複生産,對此IMF曆史性地批準了6500億美元的特别提款權分配,滿足全球各國對儲備貨币的長期需求,提升全球經濟的抗風險能力和金融體系的穩健性。我們的職責就是敦促成員國通過對内和對外經濟政策的設計,在短期内有效地應對公共衛生危機事件,在長期内實現更有韌性、更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我還參與對成員國經濟狀況的追蹤和預測。每年,IMF都會發布兩次《世界經濟展望》,其中對全球經濟以及各大經濟體發展趨勢和增長前景的預測受到全世界的矚目。這項工作的任務有兩個,一是系統性地評估我所負責國家的經濟基本面、經常賬戶、外彙儲備、資本流動等狀況;二是識别潛在的金融風險,就貨币、财政、金融等政策組合提供适當的建議,以維持成員國經濟的穩定增長。
與此同時,我還與同事進行着多項學術和政策研究。目前我們關注的重點是能夠對抗氣候變化、促進綠色轉型的經濟政策,例如如何衡量碳定價、提高碳稅、綠色投資在内的一攬子政策所産生的經濟效益,如何在國際層面推動各國政府的政策協調和一緻行動,以及如何與各國央行和各大監管機構合作創造綠色金融網絡。雖然身在美國,我卻時刻關注着國内的發展,從事着與中國“碳中和”目标、房地産市場、科技創新等相關的研究,在跨國實踐中吸取他國的先進經驗,争取為我國的經濟發展獻計獻策。
未來,我希望能夠成為熟悉國際金融體系規則、了解未來金融發展趨勢的專業人才,為我國金融外交事業添磚加瓦。從清華五道口到國際貨币基金組織,我能夠走到今天,除了個人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學院的培養,和我身後一個更加開放的中國。由衷地希望在走向國際舞台的道路上有更多的同行者和更多的五道口人。